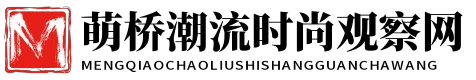两年前的旧稿:活着——命运呀,哎呀

转眼间,从我观看《肖申克的救赎》这部影片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。这两年的时间里,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,我的生活就像一本充满伤痕的口述史。今天夜晚,我像个开水壶一样哭了一整晚,这让我思考自己究竟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研究。我翻出了这篇旧日文章,它激励了我,让我相信自己还有可能继续前进。
今天,我看了一部纪录片《番客》,虽然没有一个特别触动我的部分,但它却让我哭得面无人色。我沉迷于近代史上的三次大移民遗迹,因为我想听到那些被淹没的声音。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庸碌的人,没有进入他人的世界去聆听他们的声音,而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知识带来的满足感。在二十一岁之前,我甚至不知道日本遗孤是什么。但是我仍然希望留下一点点言语,与更多人交换感动。

回顾《番客》,其时间与空间是模糊不清的,只有战前的暹罗,那是一片遥远而没有具体影像的地方,以及战后弟弟给哥哥写信的时刻。在二手玫瑰表演实践中,那里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。他们用东北话表演“舶来品”——摇滚,他们舞台设计更像是明清时期元素,而借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曲种。他们展现的是满洲特色,而不是那个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,他们从未与工人群体有过关系,只展示大地的力量。而在歌曲《命运》中,以戏谑口吻提出了几个问题:“命运呐/生存呐/为何让人受罪/为何认为人去流泪/为何人与人作对”。《番客》以一种浪漫的手法回答了这些问题。命运确实苦难,但穷也苦、打仗也苦、变迁也苦。但我们可以逃避,可以等待。而保持情感联系,也是消弭矛盾的一种方法。这意味着这些问题超越了地域,不同风俗只是表现形式,不是本质。人们对鬼神世界叙述,是对现实世界映射,无论我们如何心理,我们永远寻求“团团圆圆”。